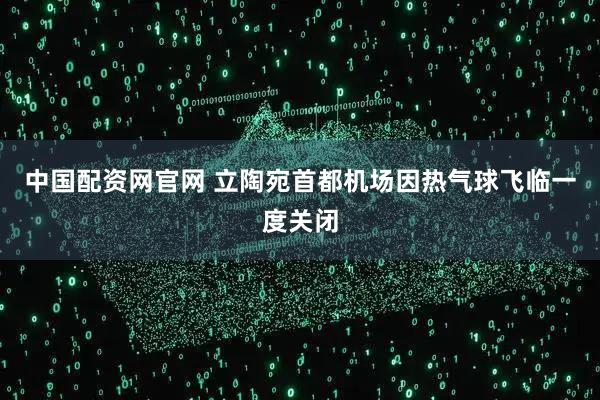书柜上的书籍因长年累月闲置,封面蒙上一层淡淡的痕尘,随意抽出一本《万历十五年》,翻开一页,书页上出现斑斑霉点。
江南梅雨季,空气潮湿,万物皆易发霉,何况书乎?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写道:“五月湿热,蠹虫将生。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。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,历经湿热的五月,倘若夏天不晒书,必然会生出书虫。
旧时苏州的书香人家,一出梅,入了伏,便开始着手晒书。江南人晒书讲究仪式感,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《上善堂藏书纪要》中介绍了晒书的流程,比如,晒书时间上,要求“曝书须在伏天,照柜数目挨柜晒,一柜一日”、晒书方法上,要求“晒书用板四块,二尺阔,一丈五六尺长,高凳搁起,放日中,将书脑放上,两面翻晒”、晒书切记“恐汗手拿书,沾有痕迹”。
当年,我的祖父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藏书爱好者,书房内四壁书橱。
每至三伏天,他便关照起儿子们,先在院落里,搭上一个板架,再将二楼书房中满架的书,一摞摞抱下楼来,一本本摊开在木板上。烈日底下,既能收湿干燥,又能驱除书蠹。
后来,祖父携一家老小“下放”到苏北乡村,每每回忆起那段三伏晒书往事,胸中五味杂陈,清代书画家潘奕隽曾写下一首晒书诗:“三伏乘朝爽,闲庭散旧编。如游千载上,与结半生缘。读喜年非耋,题惊岁又迁。呼儿勤检点,家世只青毡”。这一幅呼儿唤女晒书、翻书的场景大抵只能出现在梦境里了。他彼时心境一如叶辉《晒书记》所述:谁都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人生,但并未永远哑忍,偶有片刻光明而总是转瞬熄灭,活在逆境却不忘辨认真理,即使到头来还是活得艰辛。
《世说新语》里有一则典故:“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,人问其故,答曰:‘我晒书。’”可是,郝隆的肚皮上并没有放着书,言下之意就是,书在我的肚子里呢!这番变相炫耀满腹经纶的凡尔赛之举,将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具象化了。
乃至清朝出了一个模仿者朱彝尊更是“青出于蓝”,将晒肚皮作为毛遂自荐的营销手段。有一年,朱彝尊躺在太阳底下裸晒,恰好微服私访的康熙皇帝路过,他好奇地凑过去问:你在干什么呀?朱彝尊说,在下空有一肚子学问,却无用武之地啊!康熙听后,觉得此人才华横溢,在他中举后,册封其为翰林院检讨,把修撰《明史》的任务交给他。
2024年,我来到湖州南浔古镇,恰好,那里正在举办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城市主场活动,上千卷古书典籍走出了“深闺”,爱书者可一边翻阅历经时光洗涤的书籍,一边享受传统文化的滋养,晒书不是目的,而是成了宣扬文化的手段。
在这个碎片化信息时代,阅读方式悄然剧变,从纸质阅读模式切换到电子阅读模式。纸质书和电子书博弈此消彼长,一如发明了汽车,鲜少有人坐马车,这是一个道理。雁渡寒潭,随着运营成本飙涨、互联网冲击,传统书店的生存空间饱受挤压,终抵不过大势所趋,它们在城市中逐渐衰落、凋零,这是一场精神与现实碰撞后的败落,纸质书将何去何从?
书籍自诞生起,就成为引领人类认知世界的窗口,记得小时候,每个暑假,我在天井里一本本晒着连环画,任凭烈日照在屁股上,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纸质书,滋养着我的童年、少年……又到一年三伏天中国配资网官网,屋外,阳光正好,我抱着书,一本一本摊开放在木板上,彼时,书籍温暖,时光安然……
卓信宝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